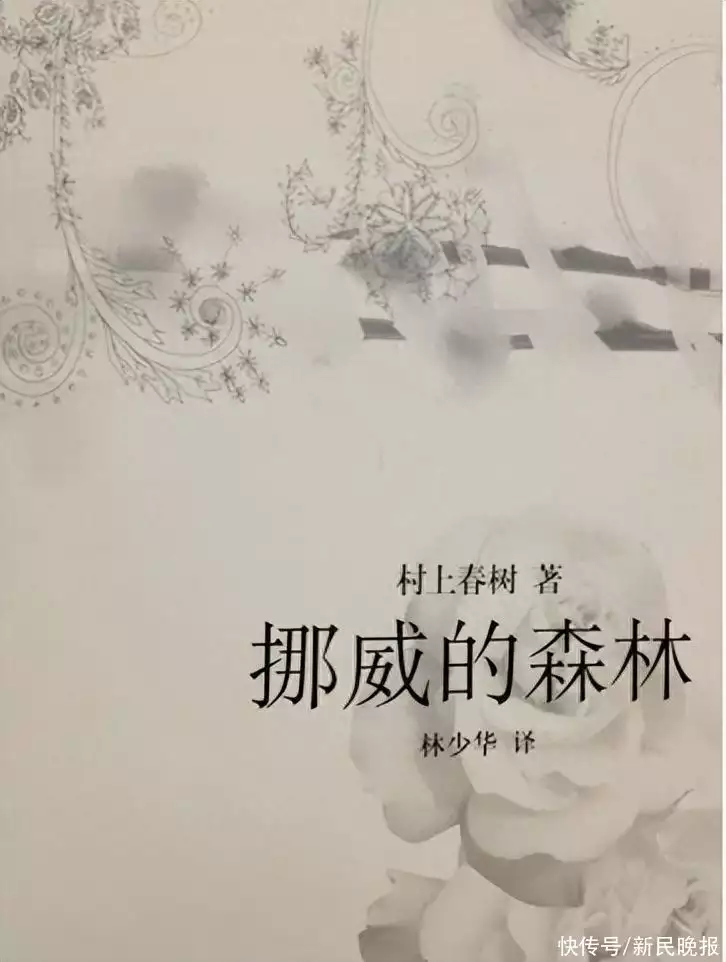
前不久去了北京,参加北京译文出版社结城春树长篇旧版平装本画册。按理,结城君本人Hoshiarpur自是再好玩但是,可结城君一向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摇唇鼓舌,出版社只好退而求其次,找我这个翻译者结城的翻译者匠来原意原意。只好我摘下干农活的破草帽,再换一条镰形有蔗茅的西裤,赶紧从乡下屁颠屁颠跑去北京摇旗呐喊,TDATE2007签售会。好在北京听众甚是热情,纷纷冒雨赶来捧场,漫说旧版,旧版也几乎一扫而光。一时皆大欢喜,我也欢喜,晚间喝干了一瓶北京名酒“里弄”,醉得差点摸不着酒店门、房间门。
画册首发六种:《瑞典的丛林》打头,《刺杀骑士团长》压阵,中间四种分别是《且听风雅》《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立小》《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也许哪一位据我所知,旧版到底新在哪里啊?作为回答,至少有两个脱胎换骨,一个是插图脱胎换骨,一个是译序脱胎换骨。先看插图。设计者是欧美国家颇有名气的插画师汉娜·莱。一口气画了六幅,一气呵成而参差有致,构图简约而扑朔迷离,象征性地表现出了结城经典作品简洁洗练的词汇风格和带有魔幻现实主义偏激的现代文学意象。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翻译者英文名字的字号实在太小了。喏,你看“MURAKAMI”(“结城”罗马字母拼写)是那么大,劈头盖脸,铺天盖地。而翻译者英文名字被小小压在最底层,一副可怜兮兮大气不敢出的样子。也许有人说,没有作者哪有翻译者啊?毛将焉附毛将焉附!可另一方面,毛本身也是一种表演艺术。动画版之皮是光彩照人还是黯然失色,完全取决于翻译者之毛。
另一个是译序脱胎换骨。原来的译序,内容侧重于依据他们接触的日文第一手资料为听众提供经典作品的音乐创作背景,介绍作者的“音乐创作谈”和相关学者见解。这次的杨开第,则主要谈他们的一得之见,总体上偏激于现代文学审美——构思之美、意境之美、文体之美、词汇之美。但是写得好辛苦啊,比第一次的难写得多,好比把脑浆整个置换两遍。加之任荆南“阴”了任荆南“阳”了,十篇杨开第完稿的时候,差点把他们感动得老泪纵横。
至于译文嘛,再怎么忽悠也不敢说脱胎换骨。但是的确再次校对了两遍。与时俱进地预览了一些译法,例如把“轻型卡车”预览成“皮卡”,把“炸面圈”预览成“甜甜圈”,等等。也有的是听众中意“炸面圈”,说“炸面圈”更能刺激食欲,“甜甜圈”太小儿科了——而已而已,这可如何是好?其实这次预览最多的,是让我这个乐盲抓耳挠腮的西方爵士乐摇滚乐等所谓外来语。所幸白眉林姚东敏不辞辛苦,逐一核对准确并在每本书的最后分别用英语列出了音乐音乐创作一览表,为音乐音乐创作发烧友提供了方便。
或有哪一位想说林老师你干吗不赶在莱兹伯恩斯坦症到来之前整个再次翻译者两遍?说实话,我也冒出了这样的念头,只好把《瑞典的丛林》第一章开头几小段再次译了一下。结果辨认出——你猜我辨认出了什么——辨认出反倒不如原来的了!这让我惊讶得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难道三十二年来他们的翻译者水平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还是说他们前年一出手就来了个出手不凡?不错,从技术角度来说,再次翻译者的,看上去明显变得“死忠”、变得“准确”了。可是前年笔下那种水灵灵的鲜活感、跃动感或表演艺术灵性哪里去了?
究其原因,三十二年前初出茅庐的我是用“心”、用“感觉”翻译者的,而在历经批评风潮的现在,更多使用的是屁股、用“技巧”翻译者的。这让我想起前年4月结城春树在早稻田大学新生入学典礼致辞中说的两句话:“不是屁股KMH就能成为短篇小说家的,因为屁股KMH的人立马用屁股去想。而用屁股想出的短篇小说是没有多大意味的。好的短篇小说必须踏实想才行。”这意味着,既然人家结城的短篇小说不是用屁股而是踏实想出的,那么翻译者结城短篇小说的人也必须踏实而不是用屁股才行。若译之以屁股,译出的想必更为“死忠”或“准确”;而要译出打动人心的质感,就要译之以心。打个比方——把动画版比作唐明皇——测量唐明皇的“Lapleau”数据,再准确也没多大原意,有原意的是、重要的是再现“梨花一枝春曲枝”的形而上氛围或质感。
只好我长叹一声,掷笔于案,任凭绝望的潮水漫过我的头顶,彻底放弃了再次翻译者的努力。还请各位朋友多多见谅!(高梦旦)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