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映后堪称“继《仁川行》后又一亚洲地区迪拉泽血腥片”的《哭悲》,前两天总算在在线视频上架了。
但我们期盼了一年,看完之后的评价却是统一的失望,并恨不得称之为“亚洲地区第三大商业片”。

因为这部影片前期宣传的所有血腥,在剧中只是靠血浆渲染得来,感观除了头痛还是头痛。
可能它唯一保持的血腥片和声,就是剧中的男主角仍旧是一个规整的帅哥。

有杨采钰艺术风格的东南亚帅哥相貌
血腥剧中必有妖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了一个铁定律。
《Montrevault幻影》里夸饰却艳丽的苏菲玛索,《Shahdol》里癫狂却又无用的涅特列布科...每一个真正象征意义上的神颜妖娆,一定有第三部血腥片代表作。

涅特列布科《Shahdol》
班莱班县,再小众的血腥剧中也一定会出现一位让我们耳目一新的热门妖娆,这种异域是在爱情影片中都不曾见到的。

Til娅·皮艾罗丽《地狱》
那么,到底为什么血腥剧中经常再有妖娆?这些妖娆们的貌美,在血腥剧中又有著何种象征意义和促进作用呢?
今天,叔就跟我们盘盘由妖娆们演绎出的这种血腥美学。
01

血腥剧中的坏女孩型妖娆:
展现出暴力行为与冲动
我们通过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血腥剧中的妖娆艺术风格是有规律变易的。
不同的妖娆脸庞,会在故事情节中带来不同的促进作用。
早期最典型的血腥片妖娆大多是能争夺人视线的坏女孩型。

《血与黑亮片》
她们的面容上一律有著大量感面容,眼睛、鼻子线条尖锐深沉,年轻漂亮,身材热辣,有著属于大帅哥的纤细和端庄。

而将坏女孩型妖娆批量放进血腥剧中的第三人,就是我们熟知的恐怖影片。
恐怖影片眼中的长发妖娆,是展现出精神血腥的最有利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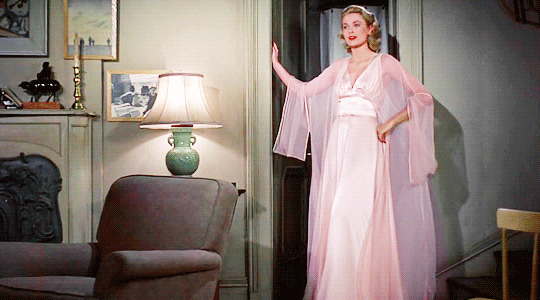
在50-60年代,血腥片是压抑下的男性幻想。
前一秒钟冰冷且天方夜谭的妖娆们,后一秒钟就被窥探、被伤害,帅哥的绝望、惊慌失措,满足了他心中的暴力行为与冲动。
当这些妖娆面越是妖娆、火辣,故事情节中的绑架、地上的大刀、墙上的小孔就越有震撼力,越细思极恐。
不过,这样的方式虽然能将血腥剧中的尖叫和绝望最大化地呈现了出来,但却也带着浓浓厌女与摧毁意味。

《棒果》的男主角蒂比·梅森莉说,这是第三部她拍过最血腥的影片。
因为恐怖影片会为了追求最真实的惊吓,偷偷将戏中发狂的假鸟换成真鸟,甚至还会对她进行偷窥和追求。

而恐怖影片却说:“长发帅哥最适合被绑架!想像一下,鲜红的血从她雪白的肌肤上流下来,衬着闪亮的长发是多么美啊!”

受恐怖影片的精神血腥影响,充斥着惊悚、暴力行为与的意大利铅黄影片,也成了坏女孩型妖娆的聚集地。

詹妮弗康纳利《神话》
因为没有审查制度限制,意大利铅黄影片将美色与暴力行为的对撞发展到了另一个高度。

《阴风阵阵》
鲜明的色彩对撞,搭配微张的嘴唇、失焦的眼神,让妖娆们的魅力不仅是火辣的、冰冷的,还是孤僻的、神经质的。



铅黄影片导演达里奥•阿基多的母亲三部曲之《地狱》
02

血腥剧中的楚楚动人型妖娆:
无用的受害者
除以好莱坞、意大利铅黄为代表产出的坏女孩型妖娆外,血腥美学中还有一种妖娆艺术风格——楚楚动人型。
她们极具东方审美下的婉转、纤弱形态,有著一张匀净流畅的圆脸型,眉眼纤细,眼型可能是杏眼或圆眼,鼻型不笔挺但娇小,像是东方画作里的古典妖娆。
个人认为最美的一版贞子,仲间由纪惠
善于运用这种美的,是日本血腥片。
在50-70年代,日本血腥片还未发展成如今的暴力行为血腥艺术风格,那时的血腥片以古典的日式怪谈为主。
新珠三千代《黑发》,讲的是一个日版陈世美故事情节
这种古典志怪文学中的人物,与与我们的《聊斋》女鬼很类似。
妖娆们通常是怨灵形象,统统有著悲惨的过去+古典审美下无法让人提防的可怜外貌。
娇柔乖顺、凄惨的八字眉,或无辜受害,或用外表来迷惑人心,伺机复仇。
《东海道四谷怪谈》
在东方世界里,这种楚楚动人型妖娆完美契合了现代人心中的血腥要素。
女子柔弱,容易被伤害,需要复仇;东方的阴阳论中,女鬼又带着最大的阴气,容易幻化厉鬼。
高桥真唯,匀净的圆脸
所以就算90年代开始,日本惊悚影片已经抛弃了古典怪谈血腥,这种妖娆艺术风格也被留了下来。
《富江》
如今我们在血腥剧中常见的复仇萝莉形象也属于这一妖娆范畴。
短脸+3:1的颅面比+圆而大的眼睛,这种极其靠近婴儿的面貌形态放在血腥语境下,近乎于一个最完美的受害者。
《镜中人》
韩国血腥片《人形师》
但也能在毫无防备下,带来最无处可逃和癫狂的绝望氛围。
03
血腥剧中的疯魔妖娆:
男现代人到底多害怕被威胁
从五六十年代下的“看妖娆惊吓”,到七十年代开始的“被妖娆惊吓”。
直到现在,复仇的、癫狂的、恶魔式的妖娆形象,已经充斥在惊悚影片和血腥剧中。
她们一律是以一种倔强和漠然的神态呈现出来,短中庭、稍近的眼间距和较短的眼裂,神情淡漠却危险。
《魔女嘉莉》
梅根·福克斯在《詹妮弗的肉体》里斯饰演一名淫荡又嗜血的女高中生,据说为了有真实性,这场火烧舌头的戏是真烧,但她仍然要维持这种疯魔之美。
血腥剧中的疯魔妖娆越来越多,女性,也变成了血腥剧中最受人瞩目的部分。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血腥剧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其实是与社会中的男性焦虑息息相关。
莫利·哈斯科在《从敬畏到强奸》提出女性威胁论:当女杀手还有女魔头这类形象充斥银幕,与女性在生活中获取的经济和社会权力同时发生,这也许并不是巧合。
70年代-90年代,血腥剧中的妖娆从“被害者”变成“加害者”的这个时间段,也是妇女在经济、社会上的地位都逐渐提高的转折点。
1973年的血腥片《驱魔人》,描述了一个12岁的小女孩被邪魔附体的故事情节。
随后的《凶兆》、《魔女嘉莉》、《猛鬼街》,追求自由主义的妇女、性开放的青少年都成为了被魔鬼附身和残害的目标。
《格亮片》、《孤儿怨》、《血腥母亲节》等血腥剧中,倔强偏执的疯魔人甚至都是母亲的形象。
将女性角色妖魔化,似乎会让男性观众短暂地从父权被威胁的焦虑里解脱出来。
但利用话语权去修改形象,就真的能阻止平等与意识觉醒吗?
如今,惊悚剧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妖娆形象,她们不止要复仇,也揭示了父权统治对其的伤害和暴力行为。
坏女孩型妖娆不应再成为展现出暴力行为的工具,楚楚动人型妖娆也未必就要成为被撕扯后的受害者。
当血腥剧中的惊恐与疯魔不再专属于女性,那时,才会创造出最纯粹的美学力量。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