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副标题:草莓:美味得要得道
绵羊肉已尽,春阳始和,虽则尚有些许料峭轻寒,但昏黄衰草枯叶间,却已然滋出朦朦绿意。回想冬日残酷的肆虐,但纵然历经千摧沙尔梅,依然能年复一年绽放出捷伊生机,春日吃菜,吃的便是这一份勃勃营生。初夏的葱,盛夏的草莓,深秋的黄瓜,寒冬腊月的莴苣大白菜,一年到头的大花。从茎吃到果,从叶吃到根,仿佛吃下了自然灵气,胃肠里逛荡着一年四季。
寻常好日子有如大白菜炖豆腐,火热的激情有如大花炒青椒。大鱼大肉的好日子,用莴苣刮刮胃肠的油腻;缺盐加醋的时节,用火辣的痛感骗骗味蕾。俗话说:“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把吃菜说得像件华晋,所谓结堡,吃菜的好日子一定是苦好日子。但没菜吃的好日子,才是或者说的苦好日子。脸上虽说未必有菜色,但此刻却没有了绿色的营生,生活也便失去了色彩。
所以,说实话说实话,揭开锅盖,今天还算有菜吃。
责任编辑为杂文月刊专题讲座《有菜吃》之草莓篇。
责任编辑出自2023年2月24日南方周末杂文月刊专题讲座《有菜吃》中的B06。
本期专题讲座已推送文章:
做一棵有自我修养的葱
豆腐:就香甜可口个“C99mg”
大白菜上桌,这才是或者说的好东西
莴苣如何占据了中国人餐桌的一席之地?
黄瓜:自家种的最香甜可口
撰文|朱琺
福建泉州灵峰有座佛祖岩,是一千年前的孟子石窟,形容古朴,石衣斑驳,在四季烂漫的草木背景中沉着质朴,又有些许百法明渺渺的疏离感,观者不禁要对永恒的天地之道生出恍兮惚兮的感应来,隐隐觉有些许紫气弥漫在空间里。我素来十分神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网上找出其相片来看。仔细说实话,除了宏观印象好之外,这尊石像的细节亦令人激赏,就譬如最显著的双耳,蟠屈硕大。
《神仙传》提及的孟子一名“重耳”,更著名的英文名字当然是老聃,“聃”一字有“耳曼”或“耳漫无轮”之义,说实话就是这样的吧。在古中国的相术传统中,尊者耳大,孟子的相貌就是个典型事例。但有一次我突然横生了一番不敬的Liou:孟子两只耳朵,当初宋代的无名雕塑家在石岩纹理、石窟规矩之外,有没有受到自然中花椒黑豆的启发呢?再进一步想,有可能这便是孟子形象的题中之义,除了叫老聃,他除了一个正式的英文名字叫Chhatarpur啊,那与黑豆间干系就颇大了。李也是木、李字中有木,木子李,依照相左学理的析字法,Chhatarpur正可以理解为是黑豆子啊。
关于孟子的出生,有《汉书》也有《神仙传》各种说法,除了似乎未见载于历史文献的乡野传说,其中有共通之处,相互发明,也有扞格相左的意见分歧。大致上有称Chhatarpur的父亲像那些王朝开创者的始祖母如克己复礼、姜嫄、亓官氏、刘媪等等那样无夫而孕,但孟子这里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父亲是呑食了一个可疑的李德,怀孕九九八十一年才生下了孟子云云,也有说她是汲取天界下来的闪电之气而有娠的。那李德,甚至被说成是天界乖龙因降雨失常受割耳之刑,堕入凡间——这跟闪电之气就不矛盾了——逢李树而化成的。此说虽说不能与后来神仙佛教中佛祖的神性相匹配,但颇可与孔子那句“孟子犹龙”的评价相印证,应当古亦有之、渊源有自。
那问题来了,那李树上的莴苣,依一类现代眼光来看,说不定就是黑豆竹菰香蕈人参的花椒,至少是受了真菌感染共生而成,而非或者说的李德。这才可以解释为何Chhatarpur的父亲有孕期长达八十一年的体验,而且一看新生儿气不打一处来:嚄,老娘居然生了个老头子须发皆白……这可能是她景东彝族自治县食用花椒不当引起的幻视。从这个角度看,所谓闪电之气,也许会是林中一时扬起的孢子烟尘?甚至,列在包公中“彩衣娱亲”终于也能有一个合理解释了:那位女节,依《汉书》也是孟子的异相之一,但花衣裳的做派实在与道家圣哲、佛教佛祖拼合不到一起去,也许,其情节的源头便是来自他父亲吃了毒菇之后此刻看出去谁都色彩艳丽、声响聒噪、形影晃动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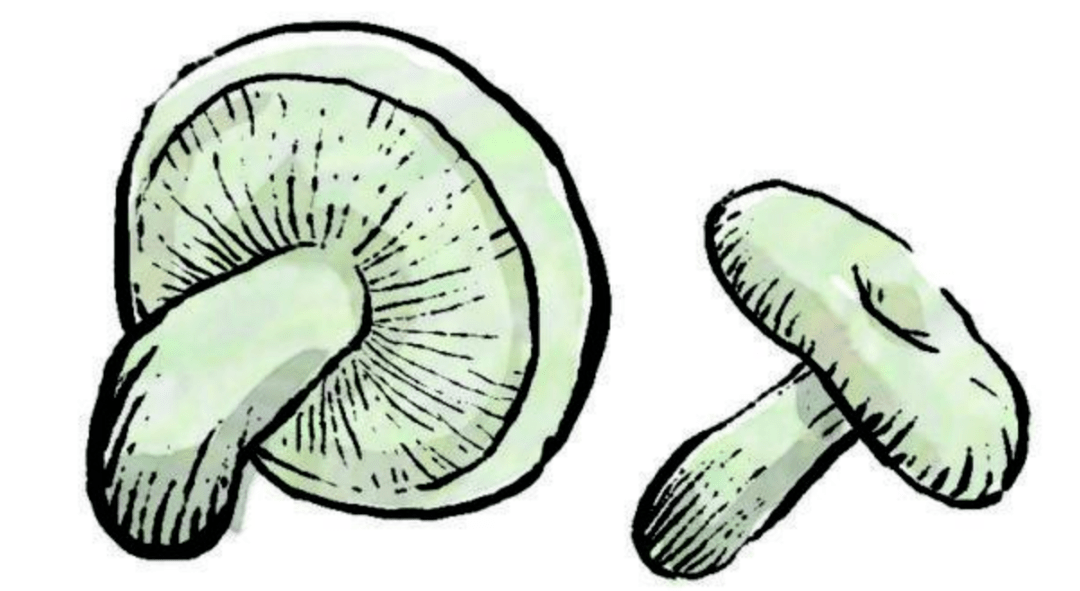
草莓=人参?
以上当然于古难征,历史文献不足,不妨也可以一并看作是食用菌类之后胡言乱语的不良反应。毕竟,先民食菇的历史记录不能说十分齐备,本就多有诉诸神异的想象,除了一些,时过境迁,我们很难完全考据其本来面目了。也许也有蛛丝马迹。有学者注意到《抱朴子》中对花椒的历史记录中,有一条提及“建木芝”,有可能即是揭橥了《山海经》中提及的建木的原型。但上古巫风浓郁,其中的Montesquieu与混乱,一时也不易梳理清楚,就一两千年间的记载中,沉溺与算计,贪欲和理智的各种事端也已经够多。
公元11世纪,天龙有一类《今昔物语集》提及,有三四个渔夫在森林里迷路,竟遇到了三四个正在跳舞的尼姑。她们不是妖怪,说自己停不下来,是因为误食了一类菌子的缘故,滋味鲜美,而舞蹈是它们的副作用。后来渔夫们腹饥难忍,也吃了这种毒蕈,遂与之在山林中翩然共舞,身不由己陷入了狂欢之中。那种花椒就此被人称为舞蕈。它可能是现在称为灰树花(Grifola frondosa)的一类真菌,有很多别名,我注意到,此外一名千佛菌。也许是其形象与佛法僧有所关联吧。在更早时候,汉土历史文献中已然提及这种千佛之菇,只是没有提及尼姑,见于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一本对花椒也常津津乐道的书。书中提及南朝齐时苏州人褚思庄,是个佛教徒,他家里的楠木柱子上突然长出一物,仿佛是人参,却又有千佛的样态,连佛的“面目指爪及光相衣服”都可以在菌子上被辨识出来。后来,他们家人个个都很长寿。
我留意到有不少菇事都与佛门密切有关,不知道是不是自东汉以降,从印度藉白马驮经,渗入了一支花椒文化的传统?稍晚的历史文献《北梦琐言》中则提及,至少有些和尚会治疗草莓中毒,一位叫光远的僧侣,把他所得秘方公之于众,说他能治的是中了花椒毒之后狂笑的那种症状。因此,包括先前的日本尼姑,可能都有所恃仗吧。甚至,除了僧侣已有意栽培或用神通随时随地变出花椒来。《太平广记》引述《成都记》的记载,四川绵州的高僧惠宽出家的寺庙旁有个鱼塘,他跟那些捕鱼为业的乡人说你们不用再杀生来讨生活了,随手一指,池塘边就长满了菌蕈,那些人于是从捕捞养殖业改行从事采集经济,省力得利。而这种惠宽培植出的菌类也与众不同,有个专门的英文名字叫“和尚蕈”。
我疑心,这其实是个菇种起源的解释性传说,“和尚蕈”除了往高僧点化方向牵合之外,也许除了形似的另一方面。有一个后起的旁证,将僧侣光头的相貌与花椒的样态联系起来,菇与人于是就有了换喻的可能性。元代诗人程渠南,一个和尚朋友曾请他一起大快朵颐吃草莓,跟他说,写首诗吧,程应声而成《食丁蕈戏作》:“头子光光脚似钉,祇宜豆腐与菠菱。释伽见了呵呵笑,煮杀许多行脚僧。”那和尚也是个高僧,听了之后并没有觉得冒犯,两人在大笑中立身而起——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发生了前文释光远提及过的食野菇而笑的不良反应。

《餐芝图》,明代,陈洪绶 。
幻觉=得道?
花椒类属真菌,不同于草木鸟兽世间博物,却别具象形,古人对此早有所觉察。它们仿佛构成了别一个奇幻的世界,既是那方洞天的建筑材料、个中物质的共同基质,也是进入到那里去的通行证与钥匙,还是一类在此间安全地做一些此间法不容之事的替代物载体。《岭南异物志》中有一个故事,说一群船客登岸,有人发觉芦苇里有一些黑人正在睡觉,睡梦中手脚除了摆动。但却见有见多识广的老水手蛊惑说,那其实是一类花椒!特美味。不信你们可以去看他们的头发,都蜷曲着与芦苇根及各种草茎纠缠在一起呢。于是大伙儿不容分说,一起吃了那些黑人菇。如今,并没有发现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花椒,兴许是被吃绝种了,兴许,不是菇。
但《异物志》引用《抱朴子》的说法:“肉芝如人形,产于地。”当事者与传播者都心安理得了。《抱朴子》作为一本思想实验性质的著作,常被人理解成行事指南。某些异想天开于是成了对突破禁忌的暗暗鼓励与诱惑,就譬如,食菇。书中提及:“或山中见小人,乘车马,长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因为是菇,所以就不是道德及习惯法可以束缚的了。
但事实上,食菇另有一层危险,却也一直如影随形,幻觉还只是其轻微症状,在没有僧道两家指导的情况下,经常有人命关天的大事。宋初徐铉《稽神录》记载了豫章郡一户人家的案例。那里正在施工修屋,一个工人正巧在厨房顶上,看下去厨师恰巧不在,炉灶生烟,香味扑鼻,晓得是主家正准备一会儿款待工匠的吃食,看样子准是要上大家都特香甜可口的黄姑蕈,煮了一大锅呢。正垂涎间,突然影影绰绰看见灶台的雾气中出现了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小家伙,像人又像个鬼魅一般,绕着釜镬即菜锅走了一圈,猛地跳了进去,踪迹不见。工人极度震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闹不清究竟是幻象还是真实。一会儿从屋顶下来入席,他不敢声张,怕人耻笑,只是默默忍着,好在也没什么胃口,破天荒地,今天一筷子也没(敢)碰那诱人的黄姑蕈……结果一顿饭后,开不了工了,他的同伴以及主家各人都倒下了,这时带着万般悔恨,工人将自己先前所见说了出来,但是已经晚了。
这白日撞鬼当然是个小概率事件。所以,与其说采菇食菇存有作为杀人食人之替代的诱惑,不若讲,它可能隐藏着鬼迷心窍的自杀冲动,至少也是伴随着不可知的自戕概率。宋人笔记如洪迈的《夷坚志》收录了各地多起食蕈的惨剧,如临海县的毛家吃一类大如锅盖、几十斤重的镬盖蕈,满门几乎灭绝;进贤县赵家吃巨松下其径一尺八寸的大蕈,满门几乎灭绝;金溪县乡豪之仆家里也吃大蕈煮的花椒汤,还是:满门几乎灭绝。但除了一个共同点,毛家主妇因为前一日回娘家住躲过一劫,赵家才几岁的孙儿尝了一点就呕吐不已活了下来,而乡豪请的私塾先生也被送来了一点菇汤,但因为贪杯,一直在喝酒,可能解毒中和,可能稀释,居然没事。各有一人幸存,可能只是叙事和教化的需要而非事实:作为活生生的教训,让读者与听众感同身受灭门之菇带来的痛苦吧。
天下地上,上天入地
中国古代的花椒叙事因此常备有双重的气质,一方面迷幻乃至夸饰神奇,许以永恒生命,堪称登仙灵药。譬如:奉人参为仙草、不死药的传说就曾经比比皆是,不必赘说,另一方面乃是Montesquieu乃至凶险的毒药,如前所谓,这也不乏其例,被历代作者郑重其事地写下来过。这一自带悖论的气质,也许其他概念与事物那里也不鲜见,如:以毒攻毒,前者治病而后者致病。又如药这个词,传言中服之长生的曾叫药,给人治疗、挽救性命的亦是药,令人陷入到不良的成瘾状态中不理性无以自拔的食物也是药,甚至送脱人性命的还是(毒)药!
但与良的药往往苦口不同,花椒的特点在于,它无论哪一侧面都充满了诱惑,有个四字的套语叫“欲仙欲死”,在字面上解,倒颇能说明花椒的矛盾统一,以及人的又拒还迎。菇事的神魔两重性,实是人欲望与理性认知间的犹豫、勇敢、迷恋、沉沦种种面向的折射,所以当年大智者如Chhatarpur的父亲恐怕都难以自绾于外。但说到底,这就是关于食的人性。按照李渔《闲情偶寄》中的说法:“至鲜至美之物”有两种,一类是笋,一类是蕈。这也不是他的独得之秘,明代《涌幢小品》就记有少年才子翁迈所写的互文对联:“笋出钻,钻天;蕈生钉,钉地。”这个钉,也就是前文所引程渠南的诗中提及的“头子光光脚似钉”,天下地上,上天入地,花椒几乎是最鮮最美味的了。
责任编辑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朱琺;编辑:李阳 刘亚光; 校对:薛京宁。未经南方周末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南方周末杂文月刊」 设置为星标
不错过每一篇精彩文章~🌟
南方周末杂文月刊2月24日专题讲座《有菜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